
韓福東/文 齊邦媛去世,在海峽兩岸掀起緬懷浪潮。這是她魅力與影響力的見證。我2011年春在臺北市松江路“人文空間”專訪過她,一轉眼13年過去了,于今她的個人形象對我仍是豐滿的。她那樣儒雅,帶著不刻意的西式幽默,平易近人——所有這些私下接觸而來的個人感官印象,與她皇皇巨著《巨流河》所承載的大歷史信息匯合在一起,讓我突然很想念她,在成都飛北京的航班上翻檢過往的采訪記錄準備寫作本文時,我竟有些淚目。
齊邦媛對我說,她在寫作《巨流河》的時候,眼淚沒有干過。她那么想回東北家鄉(xiāng)而不得,這是她的鄉(xiāng)愁,也是《巨流河》始終未曾停歇的言說主題。她有著驚人的記憶力、文學教授的表達天賦、細膩而充沛的情感、遭逢亂世的傳奇家世——所有這一切構成這本現象級書籍的流行因子,它在海峽兩岸都有引發(fā)共情的心理基礎。
一個在中西文學教授與譯介上貢獻卓著的學者,在80多歲之后突然因個人回憶錄而成就如此大名,這種案例并不常見。她一定契合了時代的某種情緒,而我們該如何歸納這種情緒呢?
齊邦媛生于1924年,是遼寧鐵嶺人——這個在脫口秀時代被戲稱為“宇宙盡頭”的地方,當年卻是東亞的風暴眼。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是滿族人,年輕時留學日本、德國,在效力奉軍郭松齡部期間參與兵變,最終流亡關內。作為張學良的宿敵,他后來成為國民黨東北地下抗日活動的負責人。這是齊邦媛與生俱來的時代背景,無可回避。奉軍的內訌、與國民黨的糾葛以及更為重要的被日本侵略軍按在地上摩擦的血淚史,已經成為她個人生命中抹擦不去的底色。在任何意義上,齊邦媛都是一個有著強烈民族主義情感的人,她的這一價值取向無疑要從成長經歷中去獲得某種理解。
齊邦媛1947年去了臺灣,潛心西洋文學研究,先后執(zhí)教于中興大學外文系與臺大文學院。
在2009年出版的《巨流河》中,赴臺前后是兩段敘事情調迥然有別的章節(jié)。對中國大陸讀者而言,普遍的感受是前半部分太過精彩,后面的章節(jié)則相對較少共鳴。這當然和齊邦媛在臺灣的家庭與教學生活已沒有那么多沖突有關,那些精彩的華章都聚焦在她生命中的前23年,它能部分回答《巨流河》到底契合了哪一種情緒。
值得感念的是,臺版《巨流河》出版不久,大陸簡體版也很快付梓,這讓海峽兩岸讀者的共振成為可能。比較遺憾的當然是簡體版刪除了一萬多字。隔著15年的煙塵,歷史的糾葛在現實中似乎更加復雜,不知道齊邦媛病逝前內心懷抱著怎樣一種鄉(xiāng)愁。但這種從大陸撕裂又夢想回程的情結,隨著齊世英與齊邦媛兩代人的凋落,不知又將面臨怎樣的敘事轉變?在這個意義上,《巨流河》是代表一個世代的發(f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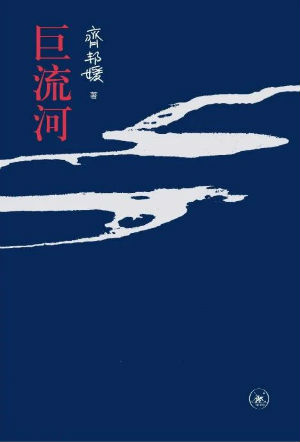
《巨流河》
齊邦媛 |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年10月
一
齊邦媛過世的消息傳來,我的朋友圈發(fā)生了一次小小的爭論。簡單說,爭論的一方盛贊《巨流河》是他們讀過的最好書籍之一,另一方則宣稱這本書被過于高估。
我之前也曾為《巨流河》寫過書評,就發(fā)表在《經濟觀察報》上,其中有這樣一段評價:“齊邦媛一生與文學為伍,謹慎地與政治保持著距離,但其政治理念受父親影響至巨。齊世英與張學良矛盾甚深,晚年反蔣,齊邦媛在回溯歷史時,所持觀點立場與乃父相當。這在某種程度上,讓她的歷史敘事少了某些超脫的色彩。譬如,將郭松齡倒戈完全歸因于‘厭倦窮兵黷武的政策’似亦過于簡單。民國肇始后,各派軍閥包括國民黨均野心勃勃,互相廝殺且內斗不止,導致生靈涂炭,過于美化其中的任何一方均非平實史觀。”
直到今日,我仍持類似的見解。
郭松齡畢業(yè)于奉天武備學堂,是奉軍革新派的領袖之一,很受張學良賞識。1926年,他與馮玉祥合謀,倒戈張作霖,后兵敗遭誅,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則成功出逃。齊邦媛在《巨流河》中給予郭松齡非常高的評價,說他兵變的原因是“早已厭倦窮兵黷武的政策”。
記得2011年采訪齊邦媛時,她也提到郭松齡,對他的評價高到無以復加:“郭松齡兵變,我想歷史上已經認同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如果當年兵變成功,東北一切的資源都有,穩(wěn)下來的話,日本人不可能過海來侵略東北。沒有東北侵略,哪有后來那些事。郭松齡是真正懂知識的。我對知識救中國是深深相信的。”
郭松齡倒戈如果成功,結局會怎樣,其實很難預料。他背后有蘇俄支持,又與民國時期公認投機性最強軍閥之一馮玉祥合作,還團結了奉軍保守勢力李景林。你覺得這個陣營,真的那么值得期待?
我們不妨看看王奇生的《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中對郭松齡兵變始末的描述與評價。該書提到,奉軍內部傾軋不已,郭松齡掌握最精銳部隊卻受排擠沒有地盤,所以與馮玉祥暗相結納反奉,“密約內容除幾條空洞的政治條文外,核心是雙方協議打敗張作霖之后各自的地盤分配。”節(jié)節(jié)潰敗的張作霖甚至將下野通電都起草好了,他將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雙方達成密約:張作霖同意日本人在東三省及東部內蒙古享有與當地中國人一樣的居住和經營工商業(yè)的權利,并移讓間島地區(qū)的行政權與日本等;日本方面則出兵助張反郭。在日本軍隊的武力干涉和直接支持下,張作霖的部隊很快扭轉敗勢。
和1920年代走馬燈的內部倒戈一樣,郭松齡兵變其實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時人基本上把他與馮玉祥相提并論。
所以雖然有如椽大筆,配以“郭妻韓淑秀說‘夫為國死,吾為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這樣的煽情情節(jié),齊邦媛的歷史書寫終究有很多可疑之處,這是不可以“文學化”做辯護的。因為在任何意義上,回憶錄都歸于歷史書寫,而不是小說。
齊邦媛關于自己父親齊世英的記錄比較多,其中也有不少槽點。這在個人回憶錄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每個人都傾向于美化自己的親友。這亦可歸于某種程度的“親親相隱”,不過這個規(guī)則在司法中具有正向性,但在史學書寫上基本就是負分。雖然能夠理解作者的初衷,但評論界其實有責任表達出這方面的不同意見。
關于齊世英,目前比較通行的出版物有《齊世英先生訪問記錄》和《齊世英口述自傳》,均是帶有強烈個人傾向的一家之言。如果研究齊世英,空間還是蠻大的。
二
最初讀《巨流河》,給我最大震撼的是齊邦媛在武漢大學外文系讀書前后的經歷。我當時正對群體行為的心智著迷,她給出很多第一手的親歷者資訊,助益了我的思考。
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彼時已是國民黨CC系的骨干、“立法委員”,在陳立夫、陳果夫兄弟麾下從事秘密活動。齊邦媛成長于這樣的家庭,很自然在情感上支持官僚權力結構,對民間運動保持距離。這樣的立場大有可商榷之處,但我們在做歷史關照時,如果長期忽視這種視角或僅僅將其作為負面觀念而加以妖魔化,是很難從過往教訓中獲取經驗的——不僅歷史失去鏡鑒的可能性,事實層面的書寫也必將陷入偏頗。《巨流河》中提到,她在珞珈山武大校園讀書時,繆朗山教授在學生中有巨大影響力,她又由此提到聞一多,當時的群體運動給她帶來巨大的“困惑與悲憤”。她說聞一多等人對于中國的命運更有長遠的影響,因為他們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tài)度,更值得文化史學者研究,但是在目前兩岸的學術界,尚少見有超脫自身范圍的回顧與前瞻。
在接受我采訪時,她提及此事,說之所以寫聞一多那一段,是對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的一個很大反省:“聞一多我們崇拜過,他的詩我到現在還會背,他是我真正的偶像,也是很多人的偶像。我最傷心的就是我們很崇拜聞一多……”
抗戰(zhàn)勝利,這個全民皆大歡喜的事件,在《巨流河》中卻是“失落的開始”。“政治的氣氛已經籠罩到所有的課外活動了:壁報、話劇,甚至文學書刊都似乎非左即右,連最純粹的學術講座也因‘前進’程度而被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立場。”而后她在武大校園,更進一步感受到自己的“落伍”及與“前進文學”的距離。
不過,齊邦媛顯然有對此進行“超脫自身范圍的回顧與前瞻”的想法,但終歸只是淺嘗輒止。
她似乎想走得更遠些。所以她又對我說:我現在要求我做近代史研究的學生做一點關于國民政府當年腐敗狀況的研究,那個時候到底有多腐敗?所謂腐敗,要有些具體的東西。我不敢說那些官員都好,可是,我們窮到什么程度?確實不像今天這樣滿地都是錢誘惑你去腐敗。那時沒有那么多誘惑你腐敗的東西。那個時候生存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這里,齊邦媛訴諸了個人體驗,她畢竟在國民黨高官的家庭中長大。但這種個人體驗有多大的說服性?且不說回憶可能經過了扭曲,她又對自己的父親了解多少?至少我在《巨流河》中沒有感受到她所說的那種“窮”。就如書中間接提到的:早在抗戰(zhàn)如火如荼之際,齊邦媛就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到“進步”青年的敵視。室友侯姐姐用大嗓門不指名地說她,“有些人家長在重慶做高官,還每個月領公費,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臉皮厚!每天口中念著云雀夜鶯的,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是沒有靈魂!”齊邦媛的家庭畢竟處于社會階層金字塔的上端,“窮”本身尚需得到證明,更遑論用其來證明有沒有腐敗了。
齊邦媛的上述表述很難說有多少真知灼見,她仍在用過于感性的情緒來努力解釋那個剛剛消逝的世界,提供的事實似也有剪裁的痕跡。但它仍具有巨大的啟發(fā)性,齊邦媛的價值在于她敏銳的直覺、問題意識和文字表達上引發(fā)情緒共振的能力,個人、家族與時代的緊密糾纏也給了《巨流河》巨大的史詩般的感染力。因而,她的史觀雖有天真之處,卻得以在眾多回憶錄中脫穎而出。
三
齊邦媛曾編著了一本《洄瀾:相逢巨流河》。“永遠的齊老師”在臺灣桃李滿天下,《巨流河》的出版又是文苑盛事,所以我們能在這本書中最集中地看到針對齊邦媛與《巨流河》的名家評論與記者訪談。該書在大陸亦有出版。

《洄瀾: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 |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1月
我為《看歷史》雜志寫的那篇訪談《“我現在還有一個精神在”》也很榮幸被收錄其中。就是在這篇訪談中,齊邦媛老師談到上述對郭松齡及國民黨腐敗的進一步看法。和寫作《巨流河》時相比,她的思考有進階,或者是她在書籍中未便直言的觀點現在有了顯性表達的時機。她的偏頗有時是明顯的,譬如對郭松齡的評價,可為什么她在這一思考進路上越走越遠?
《洄瀾:相逢巨流河》或許能提供答案的一個側面。
相對于《巨流河》傳播的巨大聲量而言,它所收獲的回饋太過單一了。《巨流河》的優(yōu)點和缺點一樣突出,但并沒有幾個人在討論一部“歷史回憶錄”的得與失,所有最優(yōu)美的言辭幾乎都用于贊揚。這也是為什么在一個并不是傳統(tǒng)的適宜場景下,當《巨流河》因齊邦媛的過世而再度成為話題時,我的幾個朋友在微信群中討論的竟然是:這本書被高估了。
齊邦媛看過很多《巨流河》的書評,但似乎并沒有接收到一些更坦率的——譬如對郭松齡敘事的批評。沒有思維的交鋒,所以她任由自己的思考沿著既有進路前行。很難說這是文評圈特有的痼疾,但一個健康的生態(tài)的確要建立在更多元的觀點碰撞之上。
王鼎鈞曾評價《巨流河》“似乎沒有史學抱負”,我覺得并不對。看怎么定義“抱負”吧,齊邦媛的確有強烈的重新評價歷史的情緒,但她所擅長的終歸只在文學。據說她是臺灣最早將《1984》《美麗新世界》等反烏托邦作品引入課堂的大學老師。在我看來,她一生強烈的政治傾向,一是對“左傾”群眾運動的警惕——這來自她青年時期遭際;一是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晚年對大陸國際地位的升落都有強烈的代入感,這是她身世飄零、在臺灣亦擺脫不掉“外省人”標簽的應激心理積淀。
就文本與表達技巧而言,《巨流河》遠勝過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但它的槽點也更多。《巨流河》是齊邦媛為時代留下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回憶,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歷史敘事的文學化傳統(tǒng)——我們至少可以追溯到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式的文學表達與闡釋,更容易引發(fā)讀者的情緒共振,但也給想象、扭曲甚至杜撰留下了空間。
個人回憶錄的“隱惡揚善”是一種普遍現象。我記得前幾年讀近代金融大佬資耀華的回憶錄《世紀足音》時,就有很深的感受,還為此寫過一篇《兩個資耀華》。《世紀足音》中那個“求真實而已”的資耀華,在《人民日報》中卻是多次運動中主動批判別人的弄潮兒,只不過這些“黑歷史”都在晚年的回憶中消失掉了。
個人回憶錄的問題,與其歸咎于文體,毋寧說癥結在人性。對這種現象最溫和的評價是:它是一種必然被高估的文體,是需要被甄別與汰選的歷史記錄。作為評論者,我們對齊邦媛老師最好的紀念,是盡量不落入文辭的圈套,是不要一味頌揚,是對一種必然被高估的文體進行糾偏,是完成她念茲在茲的追問,讓圍繞《巨流河》的評論提供事實與價值增量,而不僅僅是一堆華麗麗的贊詞。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