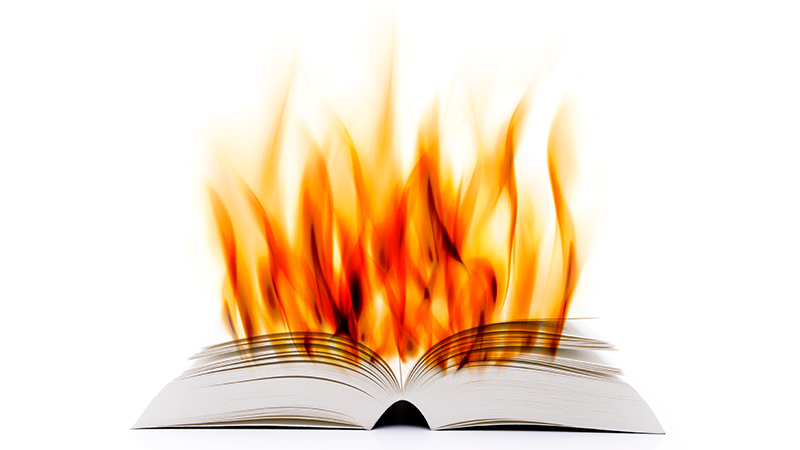
倘若我們要給知識分子加上一種義務,那么其義務就應該是通過批判——尤其是對自己的同行進行批判——來見證社會的發(fā)展。——翁貝托·埃科
不必熱誠地堅持任何一種主張。沒有人會熱誠地堅持7乘8等于56,因為大家知道這是事實。只有在推崇一種可疑的或者可以證明其錯誤的主張時,熱誠才是必需的。——柏特蘭·羅素

《密涅瓦火柴盒》是意大利當代著名小說家翁貝托·埃科的自選集,文章選自他每周發(fā)表在《快報》上的專欄,題材林林總總,不限于時政。“密涅瓦火柴盒”也是他專欄的名稱,原指一種“裝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紙制小盒”,作者常把臨時想到的靈感或念頭,順手記錄在盒子的封皮背面上,便于回家后坐在打字機前將其擴充成一篇專欄。如你所知,“密涅瓦”也是羅馬神話中智慧女神的名號,對應于古希臘的雅典娜,作者雙關命名,定然含有智性上的期許。
埃科在前言里寫道:“讀者會在這本書里看到,即使我采取的是一種調侃的筆調,但表達的卻總是一種憤怒之情。我不談讓自己高興的東西,卻總是針對那些令我不開心的事寫下自己的想法。”——不愧是“歐洲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拒絕把責任之筆綻放成一朵悅己愉人的向日葵,只在憤怒時執(zhí)筆。用“調侃的筆調”來調劑憤怒,也是一種高端的優(yōu)雅,它并非意在修飾或稀釋憤怒,而是通過適度的從容機智,矯正激情,避免偏激,使結論更加站得住腳,避免將論證過程投付滔滔湍流。
人很容易在憤怒中體驗正義,正義很容易在憤怒中滑向反面。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里提到自己認可的兩類知識分子同伴:“一種是那些知道不帶仇恨地進行戰(zhàn)斗的人;一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展開的斗爭中尋找人類命運的秘密的人。”后一種人同樣重要,因與本文關系不大,暫且略過。前一種人,與埃科的“夫子自道”正相吻合。“仇恨”與“憤怒”往往是知識分子生涯的起點,但只要他們足夠優(yōu)秀,就會在抵達終點時,將怒氣和恨意漸始消弭,唯以一派無懈可擊的理據(jù)示人。憤怒之于知識分子,頂多起到藥引之功,言論品質還得靠強悍的理性來壓陣。
不過,讀完《密涅瓦火柴盒》,重溫埃科置于卷首的那句真誠告白,我差點笑出聲來。誠然,就像伏爾泰說“希羅多德并不總是說謊”一樣,埃科也并不總是缺乏憤怒,但讓我歸納這本集子的性情特征,我數(shù)到五十都未必想到“憤怒”,位居前列的,皆與“憤怒”相去太遠。
《一本〈牙簽論〉》,開篇就興致高昂地吊足讀者胃口:“或許你們從未體驗過查詢古書目錄是一件多么有滋有味的樂事。”接著,仗著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埃科向讀者羅列了各種趣書,除《論牙簽及其不便之處》外,還包括如下名目:《棍棒的功能》——“其中列舉了大量遭到棍棒擊打的著名藝術家或作家(包括布瓦洛、伏爾泰和莫扎特)”;《德意志種族的巨大排便量》——作者在書中稱“一個普通德國人排出的糞便比法國人更多,且氣味更加難聞”;《改革派綠帽子協(xié)會》——該書“把‘戴綠帽子’的起源追溯到了巴別塔時代”,等等。我讀得樂不可支,閱讀過程中既不曾想到“憤怒”,也絕不認為作者“調侃的筆調”下藏著“憤怒”。
《海島度假小記》寫的是自稱“并非一位富豪”的作者“有幸到大開曼島一游”的見聞,那里是“一個免稅天堂”,“似乎置身于迪斯尼童話世界”則是作者的主要感受。當然,那里還是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一座避稅者的天堂,試圖在規(guī)避稅款方面有所追求的全球富豪都喜歡在那里注冊公司,中國的富豪企業(yè)家也不例外。這早已不是秘聞,埃科在沐浴海風、飽覽比基尼女郎和品嘗海鮮之余對此略加評論,不過裝點筆墨,應付文債,和“憤怒”無甚關系。因為,對一件與自己遠隔千山萬水、且根本上超出己力的事情表示憤怒,委實有點杞人憂天。相形之下,堂·吉訶德向風車發(fā)火,倒還更合理些。
《罪惡一夜紀事》是說作者某個夜晚尋訪網(wǎng)絡色情島的經歷,寫作時間是1995年。就互聯(lián)網(wǎng)紀年而論,大概相當于仰韶文化時期。我就是在那年擁有了第一臺386電腦,無法上網(wǎng),也不知互聯(lián)網(wǎng)為何物。大作家埃科先生不僅早早上網(wǎng),還著手尋覓“大量超清晰的色情圖片”,真是先驅。如果沒記錯的話,我那臺386電腦的屏幕分辨率是640*480,也就是區(qū)區(qū)30萬像素,與“清晰”壓根不沾邊。在該文里,作者的確遇到了憤怒的事,他亢奮過頭,著了某個網(wǎng)絡釣魚客的道:美國猶他州“一名極其嚴肅的道德主義者”許諾提供“超清晰色情圖片”,騙取了埃科的信任和郵箱,卻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對埃科嚴詞訓導,說他“有心理疾患,沒有朋友(更沒有女朋友)”,還說,“如果我(埃科)的祖母知道我的所作所為,一定會因為動脈瘤發(fā)作而被我活活氣死”。這事猝不及防,埃科看上去有理由“憤怒”一下,但他沒有,他只是覺得好玩。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此刻已是凌晨三點了。整夜的色情大餐把我折磨得疲憊不堪。我終于睡下,并夢見了成群的綿羊、天使和溫順的獨角獸。”
不管作者打算暗示什么,“憤怒”總不在其中。實際上,埃科在本書里展示得最充分的,就是俏皮和貪玩,以及無與倫比的機智。在《糟糕的〈第五交響曲〉》里,他以更加盎然的興致,介紹了一本“有趣的集子——《退稿信》”,該書“專門收錄文學巨著遭到出版社拒絕的評語和回信”。作者以某種涉嫌騙取稿費的作風,大做文抄公,整頁整頁摘抄例句。他顯然洞悉讀者的興奮點,即,幸災樂禍是一種難以割舍的人之常情,再純粹的文學愛好者也愿意了解成名英雄的倒霉經歷;倘讀者幸災樂禍之余還能萌生勵志之情,則作者善莫大焉。受到埃科鼓舞,我且摘抄幾個片斷,以饗讀者:
“也許是我生性愚鈍,但我實在無法理解這位先生怎能將長達三十頁的篇幅耗費在描寫自己如何輾轉反側,無法入眠的場景上。”——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
“關于動物的故事在美國根本賣不出去。”——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
“很遺憾,美國的讀者不會對任何與中國有關的內容感興趣。”——賽珍珠《大地》
“先生,您的整部小說都被埋葬在您設計的一堆華而不實的細節(jié)描寫之下了。”——福樓拜《包法利夫人》
“真令人費解。所有的韻腳都有問題。”——艾米莉·狄金森的第一部詩歌
作者的玩興并未至此結束,在另一本文集里,我湊巧讀到埃科創(chuàng)作的幾封退稿信,收信人包括荷馬、《圣經》的作者、但丁和康德。針對康德的退稿信是這樣結尾的:“德方代理人告訴我,我社還必須同時出版這位康德仁兄的其他次要著作,共有一大堆,其中甚至包括天文學。建議切勿與這樣的人扯上關系,否則倉庫里積壓的書會堆積如山。”針對薩德侯爵的情色名著《朱斯蒂娜》,埃科輕快地表示:“這就夠了。我們不是要尋覓一部哲學著作。今日讀者要的是色情、色情、更多的色情,任何形態(tài)或形式的色情。”

我提及憤怒的缺席,當然不是諷刺埃科言不由衷。因為,埃科乍看上去有點搞笑的表白,漏泄了一個情有可原的隱憂。
通常,在無需擔心被喝破行藏之時,人們傾向于狠拍胸脯,聲稱自己具備與從事職業(yè)相關的核心美德。因此,教師總會表達熱愛學生之情,企業(yè)家總會表白自己的社會責任感,會計師總會夸口自己的誠實,政客總會侈言自己充滿民主意識,黑道人物也總會強調自己遵守道上規(guī)矩,屬于“盜亦有道”那一類。反正,文字一劃拉,美德就到賬,比電子轉賬還方便,如此惠而不費,何樂而不為呢?
埃科提及憤怒,亦可作如是觀。知識分子的即興表態(tài),也是一道常見景致,在這種場合,只有傻瓜才不會把那些切合自身角色需求的東西視如囊中之物。既然他有志于成為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就必須讓讀者相信,自己正是這樣一位整天與正義耳鬢廝磨的人。而憤怒,恰是正義的配套裝束。
休謨說過:“看來不言而喻,在這樣一種幸福的狀態(tài)中,每一種其他社會性的德性都會興旺發(fā)達并獲得十倍增長,而正義這一警戒性和防備性的德性則絕不曾被夢想到。”就是說,天堂無關正義,一個相對民主、富庶的社會,很可能是一個“正義感”缺乏用武之地的環(huán)境。我們在自然界也能看到類似情況,豐美草原上的牛羊,總是悠哉游哉地吃草,互不相擾,而實施食物配給制的豬圈和雞棚,則永遠在哄搶爭食。
埃科置身的意大利,雖非一流民主國家,但還算民生安寧,富裕祥和。“羞恥啊,我們居然沒有敵人!”這是他另一篇文章的標題,筆調仍充滿調侃,說的卻是實話。一個沒有敵人、自身也不愿尋找外敵的國家,不易孳生民族主義情緒,不易滋生深刻的社會危機。
這樣的國家雖也難免包括腐敗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筆者作為資深球迷,很早就耳聞過該國的足球腐敗,而在英、德等國,類似腐敗罕有聽聞——但不管怎么說,矛盾或問題總還處于可控之中。無論知識分子或記者如何危言聳聽,他們揭露出的問題一般不會全方位地激發(fā)出讀者的正義之心。發(fā)發(fā)牢騷是一回事,形成民族性的同仇敵愾又是一回事,只要后者闕如,就會反過來制約知識分子的言詞格局。
“一旦我不再憤怒,我也就不再有正義之怒所必需的那些結論了:我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喬納森·海特語)知識分子的憤怒會誘導民眾的正義感,民眾的憤怒會慫恿知識分子展示正義,但假如民眾處于懶散狀態(tài),這類互動就無從生發(fā)。絕望中的人民才是正義的最大客戶,我們可以想象,位居聯(lián)合國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前列的冰島等國之所以不易產生偉大的知識分子,實是由于當?shù)氐馁t明政治和富裕生活,無法匹配知識分子的正義需求。一位北歐作家倘表現(xiàn)得過于憤激,或會予人“為賦新詞強說愁”之感。
埃科有篇文章叫《民主如何摧毀民主》,雖不乏調侃,但生活在次一級輿論環(huán)境下的讀者,讀來會大感苦澀。文章大概是對時任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的媒體遭遇,有感而發(fā)。埃科撰寫此文的1998年,意大利正由貝氏主政。貝氏是位明星相十足的領導人,像我這種對國際政治并未多加關注的人,也風聞過他不少丑聞和緋聞,后者好像更多些。我們還知道他是一位富豪,意甲豪門AC米蘭俱樂部的老板。當然,今天的貝氏正在監(jiān)獄里呆著,罪名是行賄議員。對貝氏,我有過一個魯莽判斷:意大利人選擇他,主要是看中其娛樂價值,選他就為了嘲笑他。讀埃科文章,我發(fā)現(xiàn)這個判斷或許不算離譜。
埃科先是提到秘魯同行巴爾加斯·略薩的一篇妙文,該文“贊揚‘性丑聞’是民主的積極表現(xiàn)”,理由是,政治領袖“越是聲名狼藉,就意味著民眾的監(jiān)督越是有效”。埃科沒有直接否定略薩,但他提醒讀者注意當前的輿論現(xiàn)狀:“這種 (針對政治人物的)揭露通常都帶有惡意,其對象往往是病痛和缺陷、過度瘦削的身材、不光彩的家世、不文明的行為舉止等等”。接著,作者又要求讀者將心比心:“如果你每天都聽到(或看到)其他人對你身體上的缺陷或你的某個荒謬之舉指手畫腳,說你性無能,說你是個小偷等等,……無論你的意志多么堅定,你都將無法容忍。”于是,埃科亮出了觀點:
“你會怎樣做呢?你會讓自己躲藏在忠誠于你的那個小圈子里,這個小圈子里的人會安慰你,讓你別去理會可惡的造謠者,同時再次向你表示他們對你的忠誠及愛戴。自然而然地,你會認為這個忠誠的圈子構成了你政治生命的心理依靠,同時把重要的職位交給這個圈子里的人,從而形成一個極為堅固的互助圈。”
該觀點呼應了文章開頭的結論:“如此一來,那些對世界負有重大責任的人物往往對于現(xiàn)實世界一無所知。”媒體任性而殘忍的揭露,使選出的政治人物日益低能,民眾到頭來卻得承受這番低能的代價,因為,那個笨蛋依舊高高在上。此即“民主摧毀民主”。
這個觀點不乏趣味,但未必高明。埃科所指,乃是一種民主制度走向濫熟階段的富貴病,對于置身該種制度下的民眾,不失為一種居安思危;對于遠未達到該階段的人,就像流浪漢聽富婆介紹減肥妙用,難免嘴巴大張,頗為尷尬。飽漢不知餓漢饑,誠然;反之則不成立,因為餓漢總還知道些飽漢感覺,誰也不會倒霉到平生沒有吃過一頓飽飯。
同時,我們對于埃科為什么無法兌現(xiàn)“憤怒之情”,也就有了“同情的理解”。

置身濫熟的民主制度下,批評政府和政黨領袖固然依舊重要,但的確不容易給知識分子增光添彩了。正因為政府和政黨領袖始終處于媒體的兇暴監(jiān)督之下,長此以往,他們真正值得批評的地方也會逐漸減少,惡性度也會日益減弱。雷蒙·阿隆說:“公眾更愿意在報紙上找到可以證明他們不滿或要求的論據(jù),而不是找到理由承認:在一些特定環(huán)境中,政府的行為不可能會和它原來的所作所為有很大的差別。通過批判,人們可以逃避對某一措施引起的令人討厭的結果的責任,即使這一措施大體上說是令人滿意的。”
在此情形下,如埃科所說,通過“對自己的同行進行批判”,倒可能更有效些。不管該種批評能否“見證社會的發(fā)展”,它至少保持了知識分子的活性,起到某種維護槍膛的功能,避免批判力卡殼生銹。所以,在《密涅瓦火柴盒》里我們不時讀到埃科針對知識界同行的商榷和批評,它們通常總是有力和有趣的。在同類相殘方面,知識分子從不不亞于蟋蟀,好在,這類廝殺有益于文明機體的健康。
此外,當社會面臨大規(guī)模不義或國家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時,知識分子的聲音固然會被無限放大,但也會變得生硬糙礪,動蕩年代的民眾本能地期待簡單結論,他們更期待給心靈帶來安撫、而非給大腦增加負荷的觀點。休謨說過:“在戰(zhàn)爭中,我們收回了我們的正義和同情感,而讓不義與仇恨來代替它們。”我曾提到奧威爾和加繆的例子,奧威爾在二戰(zhàn)期間執(zhí)意反對英軍虐待戰(zhàn)俘,強調“民主和法西斯之間深刻的道德差異”,加繆則在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在“致德國友人的信”里,堅持“為務虛細微的思想而戰(zhàn)斗”,避免與納粹在思想上同流合污。他們的見解非常高明,但也非常不合時宜,當時就被淹沒了。
那么,在一種政治相對清明的制度環(huán)境中,知識分子無需營造慷慨、撩撥正義,倒是有條件“為務虛細微的思想而戰(zhàn)斗”,埃科在這方面體現(xiàn)了偉大。閑著也是閑著,密涅瓦牌火柴盒的封皮背面上不適宜發(fā)表高屋建瓴的讜論宏議,但不妨把筆弄成柳葉刀,實施精確的外科手術式批評。
比如,關于隱私權,埃科注意到“如今的服裝卻要刻意露出肚臍、臀部曲線、多毛胸部上的項練、凸起的陰囊”,遂鄭重提議:“相關部門的工作重點并不在于向那些注重隱私權的人士(在所有公民中,他們只是很小的一個部分)提供保障,而在于教育那些自愿放棄它的人,讓他們懂得去珍惜這種相當寶貴的權利——隱私權。”
關于現(xiàn)代戰(zhàn)爭,埃科發(fā)現(xiàn),“在新型戰(zhàn)爭中,雙方不急于消滅敵人,因為面對敵人的傷亡,勝利的一方會遭到媒體攻擊。……在新型戰(zhàn)爭中,一切戰(zhàn)略部署都要以‘博取同情’為原則。”極為辛辣。
說到政黨的組織偏見,在《清一色右派》里,埃科發(fā)明“焦距的長短”概念,提醒人們留意此類現(xiàn)象:“對于某些作家,如果我們把目光局限在他二十歲左右,那么他看上去的確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但如果我們再看五十歲的他,則又成了共產主義者。”結論是:“一張把人劃為某組織成員的清單和一張把人開除出某組織的清單是同樣危險的。”
針對人們在訴訟中經常行使“道義上的信任感”,埃科像一位真正的哲人那樣提出告誡:“‘理性的偏見’并不是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人們經常從考察某件事物出發(fā),制定出一種推理模式,之后就會覺得應該按照這種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假設和思考。”
在埃科的文字世界,批評人民遠比批評執(zhí)政者危險。批評執(zhí)政者,玩兒似的,批評人民,則意味著玩完。因此,埃科若要顯示知識分子膽識,就得在這個領域有所嘗試。他果然這么做了,埃科對于當時意大利電視臺頻頻播放庭審直播,極為憤慨,民眾卻對此類節(jié)目歡迎不迭。埃科表示,他的專欄發(fā)表后,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幾乎全是誤解和反對。一位學生模樣的讀者憤憤不平地質問他:“對于阿爾馬尼尼的無恥行徑,你難道無動于衷嗎?”天下憤青都一樣,他們不是缺乏正義,而是徒剩正義。埃科莞爾一笑,迎難而上,甚至還用一種夸張的繪聲繪色,故意激惹反對者。他這樣惡心他們:
“觀眾必須坐在餐桌邊觀看絞刑直播的場景,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犯人脖子的斷裂聲、腹部的抽搐聲以及雙腿的踢騰聲必須與觀眾咀嚼食物的聲音相融合;如果是電椅,則要讓罪犯吱吱呀呀地尖叫幾秒,最好與爐子上煎黃油雞蛋時所發(fā)出的噼啪聲相呼應。”
筆調是“調侃”的,內含的“憤怒”則不失莊重。實際上,埃科真正擔心的是,個體權利會在庭審過程中遭到漠視和剝奪。他為這個主題寫了多篇專欄,感興趣的讀者不妨移駕一觀。
總之,這位以暢銷小說和大量以博學見長的著作贏得世界性聲譽的作家,有著難得的悠閑;即便在悠閑中,即便被迫在一個“報紙越來越幼稚”的環(huán)境下生存,他也無意把筆鋒投閑置散。他試圖證明,天堂里也可以有知識分子;在不存在政治迫害的地方,敢于無懼冷落,見微知著,發(fā)表逆人民虎須的異議,同時又并不自以為正確,也是一種非凡。至于“憤怒”云云,付之一哂可矣。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